近年來,高價彩禮問題頻頻引發關注。記者調研發現,一些農村地區包含彩禮在內的婚姻綜合成本上漲,有男方為結婚花百萬。彩禮在內的婚俗成本飆升,不但違背了禮俗本義,物化了人格與愛情,而且加劇了婚姻焦慮,引發“恐婚”“不婚”等一系列社會問題。

32歲的劉輝(化名)因為彩禮“沒談攏”去年剛告別一段感情。在遼寧沈陽市長白勞務市場,穿一身迷彩服的劉輝掰著手指給記者算賬:彩禮15萬元,縣里的房子和車首付還得30萬元,女方還想和他一起置辦個鋪面,這對他來說實在有些困難。
在劉輝的家鄉遼寧鞍山市臺安縣,10年間結婚彩禮從5萬至8萬元漲到了15萬元左右。劉輝說,現在村里娶媳婦的標配是一套房子、一輛車還有四金(金戒指、金耳環、金手鏈、金項鏈)。“有人家為娶媳婦欠了饑荒,一人結婚,全家舉債。”劉輝說。
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歷時一年,調研全國14省份33個縣的一手案例發現,全國彩禮出現了持續十余年的上漲,2021年彩禮平均數約為14萬元。
狂飆的彩禮只是農村結婚成本的其中一項。除彩禮外,一些地區的男方家庭還需面對約5~10項的婚俗支出。在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,除彩禮18.8萬元外,還需支付改口費、蓋頭費、三金、酒席、拍婚紗照等費用。如果加上城區的房子和汽車,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過百萬元。
課題組研究員、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說,在一些地區,還出現男方家庭越窮負擔越重的現象。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條件不好,會要求更高的彩禮,作為婚后夫妻經營生活的成本,以此保持婚姻的穩定性。
結婚高成本給不少普通農村家庭帶來壓力。在遼寧本溪滿族自治縣三合村,產業少土地貧瘠,人均年收入在1.5萬元上下。54歲的陳大姐養了10余頭豬還磨豆腐,一年收入3萬多元。“能掙一點是一點,兒子也快奔30了,現在既怕兒子不結婚,又怕結婚娶不起。”陳大姐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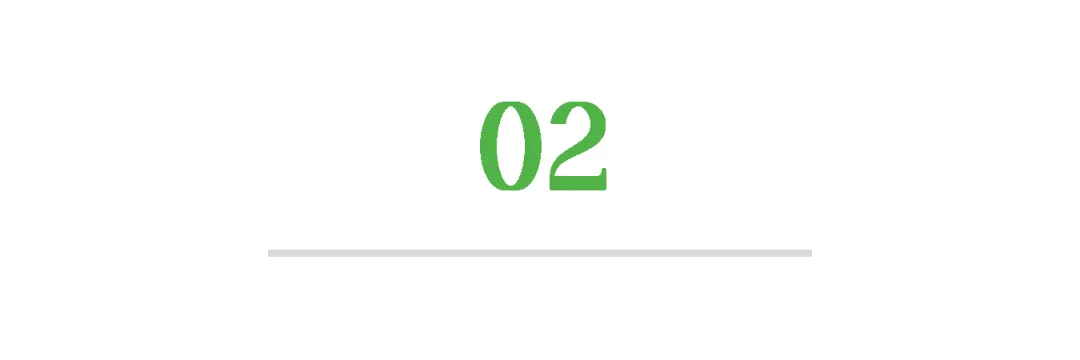
城鎮化、攀比心理、男女比例失衡,是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。伴隨著縣域城鎮化的持續推進,社會心理的復雜化、部分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加劇,治理高彩禮的難度也在加大。
調研組發現,在迅速城鎮化過程中,新一代農村青年生活預期普遍在城市而非鄉村,依靠父輩托舉進城的新建小家庭,想要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,一個最為快捷的方法,就是通過索要足額彩禮“一步到位”。
與此同時,高彩禮也是許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現危機的一種預防措施。出生在河南某縣的小凱告訴記者,原本女方不要彩禮,臨結婚前又提出增加20萬元的彩禮,“因為我家全款在鄭州買房未加女方名字,她的父母怕女兒吃虧”。
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蘇等地區的農村,出生性別比失衡,年輕女性資源大幅度向發達地區聚集,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,也導致彩禮水漲船高。
東北地區一個村支書告訴記者,留在村子里的10余個年輕男性一半是光棍,平時幾乎見不著適齡女孩。在江西省鷹潭市,2021年一位出價28.8萬元彩禮的男性被另一位出價38.8萬元彩禮的男性截胡,最終相親失敗。
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齊心說,彩禮是在多種因素長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習俗,很難通過單一政策改變。許多農民一面苦于高價彩禮的沉重負擔,另一面又樂于遵循傳統,把索要或給付彩禮當成一種人生任務。

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
當前多地將彩禮整治納入村規民約并廣泛推廣,但取得實效尚需時日。遼寧省昌圖縣河信子村黨支部書記趙國友說,許多家庭的彩禮是私下商議,村委會很難掌握,即便了解也很難有合適的身份去干預,只能進行宣傳和引導。
近年來,一些地方嘗試給彩禮設置紅線,比如山東巨野縣出臺文件移風易俗,提倡彩禮不超6萬元。受訪基層干部告訴記者,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禮攀比的風氣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,婚俗名目繁多,一些農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禮金額,也可能通過增加改口費等婚俗索要金錢,婚姻綜合成本并沒有降低。
高價彩禮屢屢觸動社會神經,折射出社會的婚姻成本焦慮。要想遏制不斷上漲的婚俗成本,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。
“關于彩禮的新風尚,各地輿論宣傳引導效果不夠理想。”齊心說,一提到彩禮,許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談。應該加大對低彩禮、無彩禮地區婚俗文化的宣傳推廣力度,并適時開展全國性的婚俗新風宣教活動,集中力量在全社會形成強大輿論氛圍。
長期在農村解決矛盾糾紛的趙國友告訴記者,高彩禮常常給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隱患,許多家庭在離婚時因為彩禮問題鬧上法庭。趙國友建議多宣傳這種反面案例,提供負面警示。
王德福表示,當前遏制高價彩禮的政策還是呈點狀分布,應該將一些地區良好的政策和經驗進行總結,因地制宜在全國范圍內推廣。一些重點省份還應該專項開展高價彩禮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,將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納入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鎮的負面清單,增強各級黨委政府治理責任,形成多層次跨區域的協同治理網絡。
來源:央視網








